《头号玩家》剧情介绍
故事发生在2045年,虚拟现实技术已经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詹姆斯哈利迪(马克·里朗斯 Mark Rylance 饰)一手建造了名为“绿洲”的虚拟现实游戏世界,临终前,他宣布自己在游戏中设置了一个彩蛋,找到这枚彩蛋的人即可成为绿洲的继承人。要找到这枚彩蛋,必须先获得三把钥匙,而寻找钥匙的线索就隐藏在詹姆斯的过往之中。 韦德(泰尔·谢里丹 Tye Sheridan 饰)、艾奇(丽娜·维特 Lena Waithe 饰)、大东(森崎温 饰)和修(赵家正 饰)是游戏中的好友,和之后遇见的阿尔忒弥斯(奥利维亚·库克 Olivia Cooke 饰)一起,五人踏上了寻找彩蛋的征程。他们所要对抗的,是名为诺兰索伦托(本·门德尔森 Ben Mendelsohn 饰)的大资本家。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检察官外传你们被包围了野性侵袭堀桑与宫村君OVA金刀秘卫之婳美人疯癫和尚之再续前缘外来媳妇本地郎神魂合体第二季我的平凡爱情人性嫉妒的化身独立也过得好的智恩第二季西瓜神级幸运儿异人之下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金太狼的幸福生活阿布·拉伊德机长相会在昨天狗狗监护权素描本你是世界的开始对我来说非常珍贵的你洛城一夜爱,不爱恐怖旅馆庇护所LoveLive!Superstar!!第二季淬火成钢黑洞
《头号玩家》长篇影评
1 ) 除了“彩蛋”的一切都很重要啊
前段时间,《头号玩家》意外成为了一部爆款电影。
说它“意外”,主要是因为这样一部充斥着游戏元素的电影不仅受到广泛的关注,还赢得了大量的好评。
在豆瓣上,这部电影收获了33.6万次评价和8.9分的评分,超过了豆瓣电影条目中98%的科幻电影。
当然,这33万多人不可能都是游戏迷,这也意味着《头号玩家》并不是一部游戏迷的电影——它由华纳制作,由斯皮尔伯格指导,面向主流大众,上映十天即在中国收获了10亿票房……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头号玩家》里有着超乎“游戏”“彩蛋”“怀旧”的更多意义,值得更加深入的探究。
诚然,《头号玩家》并不是第一部与游戏有关的电影,但仔细看下来,该片也的确进行了一些颇具新意的尝试。
比如,《魔兽世界》是将已经存在的游戏内容转化为电影,其中的人物是虚拟世界的人物;《刺客信条》略有不同,其中同时出现了现实和虚拟两个空间,尽管重心仍然完全放在虚拟空间之上;《头号玩家》则更进一步,其真正的价值在于预言性地为虚拟世界赋予了和现实世界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以此来探讨现实和虚拟的相互作用。
这是十年之前的电影不敢想的,虽然去年《星际特工》也在某些段落做出过结合两种空间的尝试,但《头号玩家》无疑是第一部敢于通篇尝试打通两个世界的好莱坞大制作。
《头号玩家》与游戏IP电影的本质区别还在于,在这部影片当中,游戏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价值受到了认可,并且开始直接和电影进行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平等嫁接。
这种认可在片中的体现是多方面的,无论是空间构成、镜头运动,还是影片结构、角色设定,都是电影文化和游戏结合的产物,这与此前单纯的IP改编存在巨大差异。
比如三把钥匙的谜题设置,就既是典型的解谜游戏语汇,也无疑有《公民凯恩》的痕迹。
此外,由于大型游戏制作往往需要花费四五年甚至更长时间,这就使得游戏往往难以与现实世界直接对接,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寓言性。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整部电影的乌托邦气质固然是由电影文本决定的,但也无疑是影片的游戏属性所赋予的。
更进一步看,影片的一个重要主题——不断地在强调要打破游戏“幻觉”,请求观众不要沉迷其中——贯穿始终,但游戏和电影却有着十分相似的幻觉机制,尤其是在3D电影时代,二者都旨在为受众营造一个巨大的虚构空间,电影依靠的是3D眼睛,而游戏依靠的是VR。
从这个角度上看,《头号玩家》其实和意大利导演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的经典作品《放大》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有媒介自指的意味。
而从这里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出视觉艺术从摄影向电影再向游戏的嬗变,在这个序列当中,空间的连贯性也在逐渐递增,直至形成一个完整的、全然沉浸的、身临其境的、令人无法自拔的体验。
应该说,电影作为一门极具包容性的艺术门类,一直在吸纳其他艺术形式的精华为其所用,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对电影的制作者和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如果不懂游戏,可能就会失去部分对电影的发言权。
要知道,随着全球“八零后”和“九零后”的成人和逐渐进入社会,那些曾经被定义甚至贬低为“亚文化”的东西成了他们引以为豪且频频引用的“圣经”。
斯皮尔伯格和他的制作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作为足以驾驭亿万级制作的金牌导演和主流价值的捍卫者,他并没有一味地关注主流价值,拍摄更多的《拯救大兵瑞恩》或者《林肯》,而是自觉地将目光投向了全新的媒介和领域。
当然,《头号玩家》也没有完全脱离斯皮尔伯格擅长的类型和手法,其实称这部电影为虚拟现实语境下的战争片也并不为过,而影片结尾叠楼区彩带纷飞的庆祝场景和《林肯》中宪法修正案通过后的景象又可谓如出一辙。
其实不光是斯皮尔伯格,从近两年的情况来看,美国主流电影工业正在一步步接纳并吸收亚文化元素,这种融合是通过两条路径实现的:一条是主流制作使用非主流话语,比如斯皮尔伯格拍《头号玩家》,另一条非主流制作使用主流话语,比如B级片爱好者吉尔莫·德尔·托罗执导的《水形物语》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
在两条路径的交汇之下,原先仅仅被一小部分人认可和欣赏的趣味变成了更加大众化的经典,也成为了好莱坞电影内容的一大源泉。
一个有趣的例证是,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的恐怖片《闪灵》在《头号玩家》中被大量引用和戏仿,这固然是出于斯皮尔伯格对库布里克作品的喜爱(后者对前者也青睐有加,《人工智能》就是库布里克去世前钦点斯皮尔伯格完成的),但更重要的是,《闪灵》并非生来就是经典,而是在80年代获得大量恶评之后由亚文化路径进入主流视野的。
与此同时,对游戏稍有了解的影迷也会发现,片中很多元素并非来自于80年代,有些菜单甚至出自于2000年之后的单机游戏,比如笔者钟爱的反乌托邦游戏《生化奇兵》、爽爆天的《无主之地》等等,这就表明《头号玩家》不仅是对80年代的ACG(动画、漫画和游戏)亚文化的一次回顾,更是对整个数字时代以来网络文化的一次整合。
当然,这些所谓“彩蛋”的大规模爆发式出现其实也并非基于某种想象中的“彩蛋文化”,而是来自于切实的压力。
笔者在早前论及《水形物语》时就曾经提到,片中对于五十年代末电影衰落情况的种种描绘放到现在仍然能够成立,只不过那时对电影院线构成致命威胁的是电视,而现在则是电视和流媒体“联军”。
如果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头号玩家》的诞生就更加值得玩味了。
确切地说,斯皮尔伯格本人近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就表示,在流媒体平台上首播的电影,不应该被允许参与奥斯卡学院奖的评选,而“一旦电影变成了电视的规格,这就是电视电影,如果好看的话,可以得到一个艾美奖,但不应该得奥斯卡。
”此番言论绝非偶然,从某种意义上讲,“院线+亚文化”与“电视+流媒体”的世纪之战即将展开,而以《水形物语》和《头号玩家》为代表的影片,正充当了这场战役的冲锋号角。
无论从何种层面和角度来看,《头号玩家》都是一部恰好处在某个重要时间节点甚至时间的十字路口上的片子。
所以,不管我们称之为“后现代虚拟战争史诗”,还是“80年代以来流行文化巡礼”,还是“近未来乌托邦科幻”,其实都不无道理,这些形容都可以为我们理解《头号玩家》的意义指出方向。
而当我们剥开层层外壳之后,影片的内核——对新技术背景下形成的权力关系的深切焦虑——也显露无疑。
虽然影片最终以一个完美的快乐结局收场,但很显然,游戏/数据/虚拟寡头在现实世界中的权力已经足以让人不安了,这些不安最终会合《银翼杀手2049》一道,形成一条完美的逻辑曲线,也就是在近未来的科学幻想中,游戏/商业寡头的权力不断膨胀,形成了超国家组织,甚至将政府挤压成了单纯的警察组织,其唯一的任务就是维护社会稳定。
在这些未来社会寓言中,终极的对抗将首先存在于政治和商业之间,底层的民众将毫无发言权(当然,《银翼杀手2049》并没有将这个问题当作“终点”)。
游戏寡头将获取一切、控制一切,而从2018年的情况来看,这种焦虑也并非杞人忧天。
虚拟和现实中的权力欲望相互助长,那些被描绘成为“技术无罪”的无人机,会不会真的有一天成为游戏寡头生杀予夺的工具呢?
在笔者对《日本电影110年》的作者四方田犬彦的专访中,四方田先生讲述了这样一个事实:日本之所以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任何一部正面展现福岛核事故的影片,其重要原因就是作为资方的东京电力公司控制了电影制作的经费。
那么在不久的未来,一部深刻揭露游戏/数据寡头的电影,还有可能存在吗?
《头号玩家》到底是一个亚文化被主流话语吸纳的开端,还是会成一个影像可以创造无限可能的时代的落幕呢?
无论是哪一种,《头号玩家》都将在电影史和游戏文化中获得它应有的地位,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一部真正的“现象级”作品,它的辐射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历史中的80年代,更关乎历史、现在和将来。
至于人类的未来会否是一片“绿洲”,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2 ) 这才是《头号玩家》最关键的那个彩蛋
以下文字内容系原创,首发于微信公众号高冷门诊部(ID:highgossip) 《头号玩家》应该都看了吧。
数彩蛋这事儿已经太多人干了,我就不掺和了。
只想从里面挑一个来讲讲。
就是“玫瑰花蕾”(Rosebud)。
以下内容涉及电影《头号玩家》与《公民凯恩》剧情细节,未观看者请慎重阅读——《头号玩家》的关键彩蛋不像高达、钢铁巨人、哥斯拉这种流行文化符号,也和《闪灵》《金刚》之类的视觉化关卡不同,“玫瑰花蕾”只出现在《头号玩家》的台词里。
为解开第二道谜题,男女主角去图书馆查阅资料,要看的是“绿洲”两位创始人的谈话。
Halliday告诉Ogden,他约了一个叫Kira的女孩去看电影,这可能是Halliday一辈子唯一一次约会。
故事的结局是,Kira在几年后嫁给了Ogden,绿洲的两位创始人也因理念不同分道扬镳。
男主角指出,在整个资料库里,这么重要的Kira只出现了这么一次,一定是Halliday对她念念不忘而删了数据。
由此得出结论,Kira就是玫瑰花蕾,更是解开Halliday谜题的关键。
绿洲的创始人Halliday和Ogden。
之后,他们才开始查Halliday和Kira看的到底是哪部电影,由此转入全片最嗨的《闪灵》场景。
那“玫瑰花蕾”到底是什么呢?
玫瑰花蕾出自1941年的电影《公民凯恩》。
影片一开始,主人公报业大亨查尔斯·福斯特·凯恩在豪华的庄园里去世,死前只留下一句令人费解的“玫瑰花蕾”。
记者由此展开调查,走访凯恩生前的亲友故交,试图解开这句遗言的真正含义。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凯恩一生的经历,却还是没弄明白玫瑰花蕾到底是什么意思。
电影结尾,人们开始清理凯恩的无比庞杂的遗产,大量不值钱的杂物被直接烧掉。
凯恩儿时的雪橇在炉火中渐渐熔化,我们才看清楚,座椅上绣着一朵尚未开放的玫瑰,上面写着Rosebud(玫瑰花蕾)。
“玫瑰花蕾”化作浓烟,成为永远的秘密,电影至此结束。
后来的几十年间,《公民凯恩》被视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玫瑰花蕾”也顺理成章地成了电影史上最重要的麦格芬。
《头号玩家》结尾,男主角解开了Halliday的三道谜题,继承“绿洲”这个虚拟世界,打开车门,迎接他的是“绿洲”另一创始人Ogden。
男主角问,你怎么来的这么快?
Ogden回答,我是坐魔法雪橇(magic sled)来的。
表面上Ogden在自比圣诞老人,备好了一份大礼。
男主角马上说,我明白了,你才是玫瑰花蕾,Halliday最懊悔的,就是失去你这位唯一的朋友。
说到这里,我想《头号玩家》里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个彩蛋已经没什么悬念了。
《头号玩家》与《公民凯恩》《头号玩家》的主线A故事,讲男主角Wade如何和同伴们一起完成绿洲的任务,最终破解谜题找到彩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成长。
表面上这是斯皮尔伯格最拿手的少年冒险故事。
《头号玩家》里的Halliday和Ogden。
而《头号玩家》里塑造的最丰满、最立体的人物,反倒是已经过世的游戏大亨Halliday。
他所驱动的B故事,本质上就是一部《公民凯恩》,情节设置几乎可以完全对照。
对照一下《公民凯恩》里的凯恩和利兰。
和凯恩的情况类似,Halliday早在故事开始前就死了,留下了三道谜题组成的遗嘱。
男主角的任务就是在游戏中破解这些谜题,从事业、爱情、友情等不同侧面来还原这位神秘的科技巨人,承担的功能就等同于《公民凯恩》里的记者。
要说巧合,Halliday故事的最后落脚点,甚至也是回到童年。
《公民凯恩》临近结尾,有人问起调查记者在忙什么,他的答案是,玩一个拼图游戏。
而“头号玩家”凑齐三把钥匙的过程,不就是在完成拼图吗?
斯皮尔伯格与玫瑰花蕾斯皮尔伯格有种强烈的“玫瑰花蕾”情结。
就在几天前,斯皮尔伯格接受BBC专访。
主持人问到他职业生涯里获得的最好的电影纪念品是什么,斯导脱口而出,《公民凯恩》里的“玫瑰花蕾”雪橇。
斯皮尔伯格还指出,他在1980年代中期拍卖购得的这件电影道具,曾被他布置在家中,目前放在办公室里。
斯皮尔伯格的记忆存在一点小偏差,他买下“玫瑰花蕾”是在1982年6月10日。
这其实是个值得斯导铭记的日子,第二天《E.T. 外星人》在北美上映。
恰巧《华盛顿邮报》完整记录了这件事,报道标题叫《玫瑰花蕾遗产》。
当时的编辑记者肯定不会想到,这位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的天才导演在多年之后会专门为他们这张报纸拍上一部电影。
奥逊·威尔斯拍《公民凯恩》,为了最后那个焚烧的镜头,一共做了三把“玫瑰花蕾”雪橇。
实际拍摄这个镜头时,威尔斯对第二条已经满意,于是就剩下了一把雪橇,后来一直放在RKO的仓库里。
“玫瑰花蕾”参加的是一场纽约苏富比拍卖会。
这把道具雪橇由巴沙木制成,长34英寸(约合84厘米),坐垫为红色,花蕾其实是白色,前期估价在15000到20000美元。
斯皮尔伯格当时在洛杉矶忙《E.T. 》上映的事,没去拍卖现场。
委托人后来接受采访表示,斯导对竞价不设上限,志在必得。
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在《夺宝奇兵2》片场。
斯导的好基友乔治·卢卡斯也很想收这把“玫瑰花蕾”,最终还是被说服了——由斯皮尔伯格参与竞拍并最终持有这件很可能创下纪录的电影道具。
拍卖过程还有点紧张。
德克萨斯石油大亨Lucien Flourney是《公民凯恩》的忠实影迷,参与了多轮竞价,可他预设了心理上限——50000美元。
结果,“玫瑰花蕾”以55000美元的价格拍给了斯皮尔伯格,算上佣金,最终一共是60500美元。
如愿以偿得到“玫瑰花蕾”后,斯皮尔伯格接受采访,他说自己很晚才接触到《公民凯恩》——18岁念大学时才看,可这电影对他影响巨大。
他认为没有任何人会尝试重拍《公民凯恩》,没有人有足够的才能和胆识去亵渎奥逊·威尔斯的创作。
斯导还透露,《夺宝奇兵》的最后一个镜头就是在向《公民凯恩》致敬。
圣物法柜最终被收为国有,工人把它推进一间巨大的仓库,镜头一拉,我们才发现那些数以万计的木箱,或许每个箱子里都贮藏着法柜一样神秘的宝物。
《夺宝奇兵》这和《公民凯恩》结尾清点凯恩遗产的镜头如出一辙,看过电影的都知道,这个场景最终结束在“玫瑰花蕾”的特写上。
斯皮尔伯格承认,这个想法其实来自监制卢卡斯,“我马上告诉他,我知道这是从哪来的”。
《公民凯恩》雪橇到手后,斯皮尔伯格表示,我只想说,这才是电影品质的象征。
“当你看着‘玫瑰花蕾’,你不会想到那些快钱、没完没了的续集和翻拍。
这激励着我在有生之年拍出更好的电影。
”作为好莱坞最大的混蛋,奥逊·威尔斯自然没放过这次蹭热点的机会。
他恶作剧般地告诉媒体,斯导买的其实是个假货,据说这件事让斯非常不爽。
斯皮尔伯格与威尔斯共进午餐之前我写过威尔斯的晚年生活,可以说是异常潦倒,在好莱坞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作,更不用说什么电影投资了。
1985年10月10日,他在洛杉矶家中突发心脏病去世,死时腿上架着打字机,还在写那些没人投资的电影剧本。
威尔斯去世后多年,他的朋友亨利·雅格洛公开了他们大量的谈话录音,出版了《与奥逊·威尔斯共进午餐》一书。
晚年的威尔斯和雅格洛。
威尔斯确实在谈话中提到过斯皮尔伯格,他甚至记不清这位后辈的名字。
当时,威尔斯写了个剧本《大厦将倾》(The Cradle Will Rock),讲自己年轻时在戏剧界的经历,准备拍成电影。
女主角定的正好是斯皮尔伯格的女友艾米·欧文(Amy Irving),她在片中将扮演威尔斯的第一任太太。
“玫瑰花蕾”拍卖过后,威尔斯邀请欧文和斯皮尔伯格到西好莱坞的Ma Maison餐馆一起共进午餐。
艾米·欧文和斯皮尔伯格。
这可能是斯皮尔伯格和威尔斯唯一一次会面。
威尔斯在饭桌上拉下脸来,求斯皮尔伯格帮他的电影募集资金,可斯皮尔伯格则更愿意向他请教关于《公民凯恩》的各种问题。
《大厦将倾》最终还是因为没有投资而流产。
更让威尔斯疑惑的是,斯皮尔伯格当时正在制作电视剧集《惊异传奇》(Amazing Stories),都没有请他去执导一集。
要知道,威尔斯生前最后一份工作是给动画片《变形金刚大电影》里的“宇宙大帝”配音。
《与奥逊·威尔斯共进午餐》里关于斯皮尔伯格的谈话。
按威尔斯女儿的说法,斯皮尔伯格甚至没给那顿午餐买单。
而那一年,他的《E.T. 》北美票房达到3.6亿美元,超过《星球大战》成为有史以来最卖座的电影。
后来,有位研究威尔斯的学者以这顿午餐为素材写了个舞台剧本,专门来揶揄吝啬的斯皮尔伯格。
“玫瑰花蕾”到底值多少钱?
不管怎么说,就以前面讲的这些故事来看,斯皮尔伯格手上的这把“玫瑰花蕾”很可能会成为史上最具收藏意义的一件电影道具。
那“玫瑰花蕾”到底能值多少钱呢?
威尔斯的研究者和影迷普遍认为,《公民凯恩》一共制作了四把“玫瑰花蕾”雪橇。
除了焚烧那场戏需要的三把巴沙木雪橇外,剧组还为童年凯恩的戏份制作了一把松木“玫瑰花蕾”。
当然,在威尔斯精心设计的镜头里,你根本看不到雪橇的坐垫,更不用说Rosebud了。
这把松木“玫瑰花蕾”曾于1996年亮相拍卖场,最终以233500美元的价格成交。
其实,市面上还出现过一把很有收藏价值的“玫瑰花蕾”。
这把雪橇并不是RKO为拍摄制作的道具,而是一件1840年代的古董。
《公民凯恩》署名编剧有两位,除了威尔斯,另一位是享有盛誉的纽约剧作家赫尔曼·曼凯维奇(Herman J. Mankiewicz)。
曼凯维奇有很重的酒瘾,威尔斯专门让制作人约翰·豪斯曼(John Houseman)盯着他,以保证剧本能如期完成。
等电影杀青,RKO办了庆祝派对。
豪斯曼和著名编剧本·赫克特(Ben Hecht)一起,送给曼凯维奇一把古董雪橇,印上Rosebud字样以示纪念。
后来,这把雪橇就被称为曼凯维奇的“玫瑰花蕾”。
曼凯维奇后人携“玫瑰花蕾”亮相拍卖会预展。
后来《公民凯恩》获得奥斯卡九项提名,最终只拿到了最佳原创剧本一个奖。
曼凯维奇始终坚称是自己独立创作的《公民凯恩》剧本,因为强加署名的事,还跟威尔斯彻底翻了脸。
2015年底,曼凯维奇家族决定将这件传家宝拿出来,亮相邦瀚斯的电影拍卖专场。
曼凯维奇的“玫瑰花蕾”最终以149000美元的价格成交,拍卖所得的一部分捐给了编剧公会设立的基金。
而斯皮尔伯格那把“玫瑰花蕾”的价格,就很难估算了。
在BBC的最新采访里,斯导借用印第安纳·琼斯的经典台词“它属于博物馆”,暗示了这件藏品的最终归属——他有意捐献给学院博物馆收藏。
至于斯导个人的“玫瑰花蕾”情结,也许正是他心底那朵从未绽放的Rosebud。
对无所不能的斯皮尔伯格来说,《公民凯恩》可能才是他一生想拍而拍不出来的那种电影。
本文系作者原创,首发于微信公众号“高冷门诊部”, 关注请搜highgossip 或扫描二维码
3 ) 无物为真,诸行皆可:你我都是头号玩家
我始终觉得,斯皮尔伯格的这部《头号玩家》,并不是科幻片,里面的世界设定,即将发生在不远的未来。
到那个时候,在每个人严苛遵守的社会身份之下,都会有一份VR所赋予的“诸行皆可”的自由,借此短暂挣脱现实的牢笼,当一次头号玩家。
——引言
1895年,路易斯·卢米埃尔拍摄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工厂大门》。
1962年,史蒂夫·拉塞尔开发了世界上第一款电子游戏——《空间大战》。
2012年,Oculus公司发布了世界上第一款VR设备——Oculus Rift CV1。
2018年,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在《头号玩家》里,用电影、游戏和VR——这三种改变人类娱乐史进程的工具,编织成一场目眩神迷的视听盛宴。
人民币玩家or免费玩家,这是个问题《头号玩家》里的世界,发生在距今不远的2045年,由于环境污染和经济萧条,为了使人逃避悲惨的现状,VR产业大行其道,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虚拟现实,“绿洲”就是其中最伟大的VR游戏。
韦德在简陋的房车里戴上VR眼镜无论是住在豪宅还是狗窝,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只要戴上VR眼镜,你就可以变成你想成为的任何人,过着你想过着的任何生活。
光吃喝玩乐还不够,多年前,“绿洲”的创始人哈利迪去世时,留下遗嘱:他在“绿洲”里暗藏了三把钥匙,第一个解开谜题的人,就能获得“绿洲”的所有权,以及继承他的巨额遗产。
这样的强大诱惑,使无数玩家趋之若鹜,拼了老命都想得到,男主角韦德和他的四个小伙伴也不例外。
在这些角逐者中,实力最强劲的就是101公司,他们的董事长诺兰,当然就是传说中的反派boss。
反派boss诺兰诺兰想要得到“绿洲”,当然不是因为什么死宅情怀,就是为了赚钱嘛。
创始人哈利迪留下的这个“绿洲”里,虚拟货币只能靠玩家在游戏里赚取,不能充值现实货币。
换句话说,“绿洲”里没有人民币玩家和免费玩家的区别。
在诺兰憨厚的设想中,如果他得到了“绿洲”,首先开放充值,把玩家分为钻石、黄金、白银和青铜几个等级。
说到这,我仿佛听到《王X荣X》《英X联X》的呼声,这些游戏的策划跟本片反派boss有什么关系,我可什么都没说,不能成为呈堂证供。
当然了,我们浑身充满正义细胞的主角韦德,肯定不同意诺兰这么搞,他穷得住贫民窟的房车,就剩在“绿洲”里寻找人生的意义了,如果开放充值,他这样没钱氪金的免费玩家,会立刻成为那些人民币玩家碾压的炮灰。
韦德所能做的,就是先一步破解哈利迪的三把钥匙。
虽然101公司财大气粗,有一批精通流行文化的宅男宅女智囊团,还有雇佣的大批职业玩家,但韦德也有几个得力帮手,以及最重要的一点——他自认为是全世界最了解哈利迪的人。
说到底,《头号玩家》的故事主线,就是一个免费玩家组团打付费玩家的故事。
至于结局如何,我就不剧透了,只给你看看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电影梗中的巨梗——《闪灵》在《头号玩家》中,使观众津津乐道的,除了炫丽的特效场面,还有就是多达数百个游戏梗和电影梗。
看着这些熟悉或者不熟悉的角色和元素,打破次元壁汇聚一堂,简直令人拍案叫绝。
我作为恐怖片影迷,特别留意片中的恐怖片梗,看到的老熟人有《猛鬼街》的猛鬼弗雷迪,有《鬼娃还魂》里住着杀人狂灵魂的鬼娃……跟其他惊鸿一瞥的电影和游戏角色不同,《头号玩家》里花大量笔墨重现的电影巨梗,就是1980年库布里克导演的经典恐怖片《闪灵》。
《闪灵》讲述了一家三口去看守山顶的酒店,由于大雪与世隔绝,偌大的房子只有他们三人和鬼。
而《头号玩家》里,这个闹鬼的酒店,成了解开哈利迪第二把钥匙的关键场所。
依靠先进逼真的VR技术,韦德和四个小伙伴在这里感受到了原汁原味的惊吓。
许多《闪灵》里的经典场景和剧情,在《头号玩家》都得到了身临其境的展示。
作为一个十年前看过《闪灵》的老影迷,好几次都被吓得一哆嗦。
比如走廊里穿蓝色连衣裙的双胞胎小女孩:
《闪灵》剧照比如打字机里自动重复的一句谚语:“只干活不玩耍,聪明孩子也变傻。
”
《闪灵》剧照比如237号房间里,一位身材曼妙的金发美女,走出浴缸投怀送抱,却变成腐烂长蛆的老太婆:
《闪灵》剧照比如电梯里涌出的大量鲜血:
《闪灵》剧照又比如酒店边上修建的诡异迷宫,主角们被鬼怪追得四处奔逃:
《闪灵》剧照特别有趣的是,《闪灵》里挂在走廊的老照片,成了《头号玩家》里的重要道具。
站在中间最前面的男子,原本是《闪灵》里男主角杰克的前世,而在《头号玩家》里,被换成了“绿洲”创始人哈利迪,边上还加了一位靠着哈利迪肩膀的女士,这就是哈利迪爱而不得的女神基拉,他的这段心碎往事,恰好成了解开第二把钥匙的关键。
《闪灵》剧照诸如此类的小彩蛋和大彩蛋还有很多,足以换来电影迷和游戏迷的会心一笑,其编排之精巧,想必也能够让普通观众大饱眼福。
“无物为真,诸行皆可”这八个字,出自我非常喜欢的游戏《刺客信条》。
在我看来,这两句话,也道出了电影、游戏等一切造梦工具的本质。
你当然知道,电影是导演穿着小背心,带着剧组演员在片场拍下来的。
你当然也知道,游戏是策划写出脚本,再由工程师一排排代码写下来的。
都是假的,“无物为真”。
然而,这并不妨碍你坐在大荧幕前,纵情投入一个个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从左拥右抱、到拯救世界,从破旧鬼屋、到钢铁王座。
这也不妨碍你拿起游戏手柄,或者鼠标键盘 ,从打怪升级、到调戏总裁,从大战异兽、到殴打老板。
都很自由,“诸行皆可”。
鉴于VR技术越来越成熟,我始终觉得,斯皮尔伯格的这部《头号玩家》,并不是科幻片,里面的世界设定,即将发生在不远的将来。
到那个时候,在每个人严苛遵守的社会身份之下,都会有一份VR所赋予的“诸行皆可”的自由,借此短暂挣脱现实的牢笼,当一次头号玩家。
如果真到了2045年,你看到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家伙,在公园晨练时,带着VR眼镜,从略有褶子的老脸上,露出一丝中二病的笑容,那就是我。
要是你看到这人突然站直了身子,双手平举,那请不要打扰我,我要开始“信仰之跃”了。
《刺客信条》
4 ) 再塑乌托邦
这是我在电影院里面哭的最厉害的一次,然后我哭着下了电梯,哭着走进星巴克,现在我写这篇影评,我还在哭。
一切将这部电影当作亚文化狂欢或一种消费符号堆砌的人,都是对这部电影的亵渎,我诅咒一切以彩蛋或考据的方式解读这部电影的人。
这部电影是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如何重新塑造乌托邦的最美好的祝愿与期待。
1 乌托邦的需要现实世界确实已经千疮百孔了,对虚拟世界的需要其意义在于我们已经无法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任何的意义。
从不知道什么时代开始,也不为我们所知的缘由,宗教的期待结束,新教的期待结束,科学的期待结束,现代社会的期待结束。
我们不得不面对仅仅余下消费与快感的一地鸡毛。
这就是为什么对这样的一部电影,我们依然只能做消费化的解读。
找到里面的所有彩蛋的表象,却无法读出里面的任何意义。
如果人类还有一次机会,能够建立起我们的乌托邦,那就是在一个统一而博大的虚拟世界之中了。
因此这部电影具有极强的时代性。
2 乌托邦的所有精神这部电影完美的展现了这个乌托邦再造的所有要素和过程。
- 一个天才的想法(霍勒迪的初代绿洲)- 英雄主义(绿洲五强)- 无私(主角将权力分享给五强)- 精英精神(五强每个人的牺牲和里面另一个高级玩家的自私)- 对资本主义的脱离(对IOI的对抗)- 共同意志(所有人的参与)- 不断的克服我们曾经错误的勇气(霍勒迪的彩蛋的意义和另一位创始人的出现)- 对真实的尊重(保留真实世界)这部电影完美的还原了这个乌托邦建立的所有要素和细节,这里面的每一个其实在我们的真实世界都已经失去了。
天才早早的被现实的名利或自尊心腐蚀,普通人丝毫也不相信自己可以成为英雄,仅仅能够无力的苟延残喘自己破碎的生活,在我们有机会的时候,用法律的框架彼此限制和干预,还以为这是最伟大的发明,不仅自己否定成为卓越的可能,还以犬儒的方式嘲弄一切成为卓越的尝试,一头扎进资本主义文化,要么拥抱消费,要么拥抱金钱的游戏。
然后回到网上互相攻击和谴责,以他人的苦难和不利的境遇为乐,将所有的错误归咎于他人而不是我们自己,接受网上一切将他人描绘的愚蠢或背德的描述,逃离真实的压力和重量,在互联网上寻找一些轻巧的娱乐。
因此当这些伟大的精神被恰如其分的展现在一部电影中的时候,这个展示本身才显得如此动人,这种感动本身蕴含着对逝去的珍惜和感怀。
向一切美好都丧失之时,人们于夜里围坐在废墟与营火前,想起往日的荣耀和美好,没有人能忍住哭泣。
3 一部完美的电影,也许不那么完美这是我看过的又一部完美的电影,在融合商业电影与理想主义上,这部电影已经做到了极致。
商业的部分节奏把握非常精确,理想的部分塑造的完整,立意很高,在电影院中丝毫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看完之后又有持续的触动和思索。
但不那么完美的部分,就是这部电影实在是太理想主义,里面的正面角色完美无暇,而其他人也异常的无私,让这部电影丧失了不少的真实的深度。
不过如果理想主义最完美的形态,不考虑其真实性的形态,确实也需要一种表达,历史上很多戏剧和文化作品,也都在做这样的描述,在对理想的全面刻画上,这部电影已经做到了几乎完美。
4 重回现实现在我坐在这个星巴克,电影中的理念世界在我头脑中一点点消退,现实残酷的真实感再次袭来。
我四周是懦弱又短视的人群,目力所及之处全是消费的符号和价格标签,若有人许诺对于这个花花世界的掌控,怕是很少的人能够抵御这样的诱惑。
但是,但是,乌托邦确实就要建造于这样的世界上,包含了对我现在看到所有人的改变,和我看到的所有事物的改变。
我们将要付出比电影中可能多出百倍千倍的努力,并花上更长久的时间,才能哪怕仅仅是拖缓这个世界坠落的速度。
而我们可能要再花上再有千倍的时间和力量,才会让乌托邦真的降临。
在这千万里苦路之上,有这样的电影聊以慰籍,并让我们一睹乌托邦的光芒和美好,无数次提醒我们这一切值得期待,并为之无数次重新出发而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这部电影也就够了。
继续征程吧。
5 ) 头号玩家 其实是对宅文化的嘲讽
转载自S1 作者:windtrack不谈原著 只谈电影看完电影之后,相比铺天盖地的彩蛋相比,我最大的疑惑不是这电影到底有多少彩蛋,而是一个2025年出生的,活在2045年的小屁孩子,为何会对一个上世纪80年代都谈不上主流的雅达利游戏这么熟练?
别说2045年已经有绿洲这么好玩的根本不用出来的游戏了,就以现在的主流玩家,从后PS2世代开始接触电子游戏的玩家而言。
有多少人知道雅达利主机,见过实物,能说出5个以上卖座游戏?
反正从FC开始玩游戏的我也就见过一次雅达利2600的实物,游戏也就知道个大崩坏的ET。
其实电影中还有一个严格来说算是BUG的镜头,第三把钥匙解锁时的游戏Adventure是79年Atari2600主机的游戏,而最后一闪而过男主操作游戏的手柄,却是5年后才发售的Atari5200主机的手柄造型,虽然略有不同,但2600摇杆加红点的造型太过经典,绝不可能是带键盘的手柄。
当然那些流量营销号蹭热度彩蛋贴并不会告诉你这个错误。
这同样也说明,其实大部分观众,可能包括电影制作人员,对将近30年前的游戏,也根本谈不上精通。
那么又回到最初的问题,2045年的青少年,居然对一款80年前的游戏这么熟悉?
显然这是不现实的,那么为什么主角能够这么熟。
其实影片已经解答了我们的问题,主角研究了哈德利平生所有喜欢的游戏、电影、音乐。
而研究的动机,当然不是因为他喜欢这些游戏,他只是想获得这些股权,在现实生活翻身,买上一个大平层公寓天天醉生梦死,实际上他也这么干了,而且每周还要维护两次不让死宅玩游戏。
这很宅文化么?
宅你妈个头!
再看看女主角,除了一个生生安上的阿基拉摩托和长得很像DOTA2花仙子的脸之外,我几乎找不到这个人物和游戏文化能挂上钩的地方。
她寻找钥匙的动机是为了在IOI过劳死的父亲复仇,然而我想问问,你们天天在绿洲里NEET,欠一屁股信用卡,IOI给你们工作让你们还账,诚然这个工作确实是不太人性,但比你这种NEET对社会共享要大的多吧?
欠债还钱不是天经地义吗?
如果你真的像电影里那么牛逼,twitch直播万人迷,在游戏中挣的虚拟货币早够替自己父亲还账了吧,然而呢?
所以总结来看,男主女主,根本谈不上严格意义的亚文化爱好者,他们都是和现在你随处都能看到的蹭热度流量营销号一样以利益驱动来搅浑传统亚文化领域的那一勺老鼠屎。
而整部游戏里真正的宅是谁?
是那个不敢跨出接吻那一步,葬礼上还要用Star Trek的LOGO的程序员死宅哈德利。
而这个死宅,整部电影全程都在被嘲讽。
和女朋友去看电影什么都没发生,开发的游戏导致社会退步,甚至被暗示是个基佬,沉迷虚拟世界吃不饱饭。
仔细想一想,这不就是当今社会嘲讽死宅的常用手段么?
单身,电子**,沉迷二次元老婆被家长怀疑**。
斯皮尔伯格用那么多视觉特效里毫无意义的彩蛋,其实埋藏的还是嘲讽死宅这个主题。
有人说的好,头号玩家是一场伪宅的盛宴,没错。
现充们带着女友到影院,看这是自由高达,那是机械暴龙兽,11岁小孩玩的是盲僧。
女友哇,你懂的好多。
然后两人看完回家和片中主角一样在大平层公寓转椅上来一发。
尽管他们不知道元祖高达,分不清钢铁哥斯拉,可能根本没听说过真人快打,但是不可否认正式这样的人群才是头号玩家真正的票房中坚,才是斯皮尔伯格真正的客户群体。
而死宅呢,自己一个人默默看到结尾字幕放完所有版权列表并回忆对应片中出现的角色后,还是回去现实世界隔壁吃肥宅餐喝快乐水填饱肚子。
其实你只是一个没有契约的IOI员工,根本没有快乐。
快乐只永远属于现充,属于赢家,不属于享受游戏的人。
这不就是这部电影告诉你的真实吗?
6 ) 媚宅媚不明白的商业片
首映得夸一波杜比,杜比影院真的是一种享受。
然后一句话总结这部电影:通过老套故事来表现出的美国的前流行文化彩蛋大集合。
先说优点吧,这部电影真的会让一个了解美国宅文化的宅男感觉非常“温馨”。
电影确实穿插了各种美国前流行文化的彩蛋,无论是游戏还是音乐,或是电影小说等。
忍者蛙,街霸,光环,真人快打,回到未来,卡拉狄加,早餐俱乐部,千年隼,类似的彩蛋数不胜数。
正好我去年看了一本知识量涵盖更高的美国宅文书籍《宅人约会指南》,确实有很多契合之处。
在美国,Nerd这种宅男不是人人能当的,他们几乎人人都是Geek,因此这些人也确实不善于社交。
这部电影估计让这些Nerd群体感到了些许温暖。
同时电影在最后也确实树立了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游戏终归要回到现实,这是我很欣赏的一点,毕竟宅归宅,不要过于自嗨。
接下来说说我为啥给了7分。
第一,这部电影并没有“玩”到及格。
游戏中致敬了很多美国前流行文化,但是大多数都是点到为止——我估计也是没拿到版权。
这就导致整部讲“玩”游戏,“享受游戏乐趣”的电影,竟然没有很多有代表性的元素出现。
没有RPG祖宗龙与地下城出现,没有战棋类出现,没有boardgame,没有tcg,没有星战,甚至没有任天堂索尼和世嘉。
没错,真正给我们留下乐趣的游戏,你在这部电影中通通都看不到。
那叫个鸡毛第一玩家!
第二,人物形象过于标签化扁平化。
人物性格单一到爆炸。
好人拯救世界,坏人自私自利,最后坏人被好人感动,放下屠刀。
请问一下,我在看小马宝莉么?
这个故事不改主线,你把人物形象刻画的深刻一些岂不是更好看?
还是说这样就不能用超炫的特效来骗傻子掏钱了呢?
可是既然是面对Nerd群体,就要有被Geek质问的准备啊。
第三,世界观超级奇葩。
2056年(左右吧),世界没有新的流行文化产生,仍然疯狂的迷恋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文化产物?
游戏设计师兼董事长(岩田聪一类的天才)竟然把公司的命运转让给一个不懂管理的玩家?
大家忙着脑后插管,忘记自己现实中过着什么日子?
反派想要获取利益,但却一直采取正当手段跟其他玩家竞争(连个外挂,刷分的行为都没有)?
老百姓在大街上带vr还不能被车撞死,不影响交通?
一个能拿炸药炸贫民窟,能带枪杀人并且没被搜查的公司,竟然被警察抓走从而结束自己的犯罪生涯?
我玩过不少美式游戏,美国的文化行业创造者其实大多数都想当上帝,希望自己像托尔金那样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出来。
可能这部电影的原本小说作者也是这么想的吧,只可惜电影表现的太浅薄了。
总之,电影嘛,Nerd们值得一看,图个乐呵吧。
如果不是宅文化爱好者,还是别看了,没啥意思,就这样吧……
7 ) 眼镜?
听说头号玩家承载了电子游戏迷们的过去和未来?
影片很不错,看的我很激动,里面好多见过没见过的梗,玩过没有玩过的游戏,都让我觉得异常兴奋。
但是对于一个专业的视光人员来说,还是有几个故事的情节设定让人觉得挺有意思。
首先,这个故事是发生在2045年, 科技那么发达了近视眼问题还没有解决掉啊?
真的人好让人头疼啊,看了电影真的是感慨万千。
再看看我们的男主 ,因为近视镜片是凹透镜,远视镜片是凸透镜,所以一般带近视眼镜的人,眼睛和周边会缩小,远视眼镜会放大。
但是整片电影看下来,无论是男主还是最后的大佬,虽然一直都有眼镜傍身,但是他们的面部都完全没有形变的痕迹,这也就说明,两人带的是平光镜,两人完全没有屈光问题,可能是为了塑造角色,给安排了眼镜的形象设计 大佬的眼镜框很不走心的带歪了,明显的是左边高,右边低,如果说按照常规瞳高来看的话,左眼的瞳高必然是不合适的,这样如果是带度数的眼镜,可能是会造成复视或者头晕恶心的。
另外,大佬的眼神看上去也是怪怪的,仿佛走神了一样。
大佬的眼镜框很不走心的带歪了,明显的是左边高,右边低,如果说按照常规瞳高来看的话,左眼的瞳高必然是不合适的,这样如果是带度数的眼镜,可能是会造成复视或者头晕恶心的。
另外,大佬的眼神看上去也是怪怪的,仿佛走神了一样。
不过怎么说,这部影片个人觉得都值得去再看一次,下周有空,再去二刷,希望会有更多发现。
8 ) 【C+影评】头号玩家:时光倒流±四十年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大概是整个好莱坞最难以被定义,也是最伟大和最有影响力的电影制作者之一。
在四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他执导的题材横跨人物传记、动作冒险、科幻甚至动画,更不用说浩如烟海的监制作品了。
而年过70的斯皮尔伯格也依然保持了旺盛的创作力:在度过了十年前的相对低潮期之后,现在的斯导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二次复兴。
在四十年间,有许多电影人前赴后继地试图去捕捉和模仿斯皮尔伯格的成功秘诀,尤其是他对幻想和冒险题材的处理方式,但除了嫡传学徒J·J·艾布拉姆斯和肖恩·利维之外,没有一个能算是真正地学有所成,而这在专攻家庭市场的迪士尼身上显得格外明显:在青年演员的挖掘和调教上,科恩兄弟在《恺撒万岁》里挖出的阿尔登·埃伦瑞奇,虽然在《韩索罗外传》中被迪士尼指定为哈里森·福特的接班人,但无论是在《恺撒万岁》还是《韩索罗外传》的预告中,我们都会发现他的表现严重缺乏个人特点和银幕魅力;而在老少咸宜的特效大片制作上,皮克斯元老之二,安德鲁·斯坦顿(《异星战场》)和布拉德·伯德(《明日世界》)负责的大制作,以及新近上映的阿娃·杜威内新片《时间的皱折》纷纷折戟沉沙——尴尬癌晚期的后者尤其不忍卒睹——或卖弄CG特效或叙事框架迂腐,不一而足。
斯皮尔伯格的独家配方,始终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应用自如。
同样是冒险电影,其他人或许能够融入探索,神秘,勇气,刺激和希望,但只有斯皮尔伯格才能在令人感到满足的同时,深远地启发人心。
由此在这重意义上,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透过一系列成功电影作品,启发了2011年《头号玩家》小说的斯皮尔伯格,能够在2018年执导《头号玩家》电影,继而启发新一代的电影观众,真正地实现了一个完美的轮回。
充满未来主义风格的《头号玩家》,是为ACG亚文化群体,尤其是游戏玩家们奉上的一场盛宴。
和时下主流的商业大片不同,《头号玩家》不仅清晰地展示了年轻主角们是如何成长为英雄的,同时对阴谋情节和设定细节有着非常精细的描绘,这些伏笔在电影的前期可能难以觉察,但在第三幕会令人恍然大悟。
所有这些富有迷影精神的复杂内容,与两位资深NERD,原著小说作者恩斯特·克莱恩,和漫威电影改编老将,编剧扎克·佩恩是分不开的。
尽管有着如此复杂的叙事层次,《头号玩家》在斯皮尔伯格的点拨下,让观众能够轻而易举地透过复杂的情节,看到斯皮尔伯格式的“少年拯救世界”这一美好而又单纯的母题。
斯皮尔伯格和他的精英团队们在本片的视觉元素上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功夫,这让《头号玩家》成为了流行文化的嘉年华,海量的彩蛋和玩梗的幅度之深远令人瞠目结舌,简直就是将过去数十年的文化元素,用未来的笔触重绘了一样。
而斯皮尔伯格以行云流水般的叙事技巧,确保了即使你对电子游戏一无所知,也并不会影响你去享受令人愉悦的2个小时,并在最后爱上《头号玩家》。
这是因为,比无穷的玩梗更重要的,是斯皮尔伯格始终如一的那种老式情怀:在炫目和超现代的视觉奇观之下,他从来不会忘记提醒观众,去寻找并享受只属于真实世界的美好和满足感。
斯皮尔伯格对科技所抱有的乐观情绪,在这里也得到了很好地体现。
当以《黑镜》为代表的众多“黑”科技影视作品开始唱衰被科技反噬的人类未来时,斯皮尔伯格依旧坚信,并且描绘出了人性的美好一面被科技激发,并且得到升华的一面。
从某种程度上讲,《头号玩家》就是一个真人版本的《机器人总动员》+《查理和巧克力工厂》。
而对于斯皮尔伯格来说,充满着十足乐趣的《头号玩家》,也是自我的一次重要回归:在一连串优雅而又备受好评的时代片(《战马》《林肯》《间谍之桥》《华盛顿邮报》),以及几部表现不佳的幻想题材冒险电影(《丁丁历险记》《圆梦巨人》)之后,他在《头号玩家》中试图找回了早期大片中的那种令人着迷的魔力。
在任何时候,斯皮尔伯格都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电影制作人。
90年代中期之前,他一直在致力于从孩子和表面上长大,但内心依然保有纯真追求的成人的角度去讲述故事(《夺宝奇兵》《E.T.外星人》《第三类接触》);而在某个时间点之后,他开始转向更为成熟的家庭化主题,描述已经完全社会化的成年人如何重新与家庭/子女建立联系(《A.I.人工智能》《世界之战》),在这里,“家庭”的概念可以是隐喻的:比如《慕尼黑》中国家与人民的关系,《猫鼠游戏》中汤姆·汉克斯对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父亲形象。
而在《林肯》中,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字面上的家庭关系,和隐喻中的家庭关系。
恩斯特·克莱恩在小说中尽力描绘的,恰恰是斯皮尔伯格早期的那种充满童趣和纯真的魔法般力量:少年踏上放飞自我和不受约束的冒险历程。
而在《头号玩家》中,斯皮尔伯格也成功地将两个不同时代的自我风格加以融合,在令人享受大量信息的同时,从来不会让人觉得凌乱。
电影结合了粗犷的实拍和质量极高的CG效果(卡通化的艺术设计大大削弱了恐怖谷效应),在其技术结构和前瞻性思维方面也都展现了鲜明的斯皮尔伯格特质。
回首斯皮尔伯格在近年来的表现,我们很高兴看到一位经典大师的完全回归。
而纵观2018年,我们也可以肯定,《头号玩家》也标记着今年的一场非凡而又卓越的电影之旅正式拉开序幕。
9 ) 为什么我不喜欢《头号玩家》?
理论上我有每一个理由喜欢《头号玩家》。
从品位来说,我几乎可以算作一个美国宅:科幻迷,超过20年的游戏历史(主机,PC皆通),认真听过上世纪欧美摇滚,库布里克死忠粉,Monty Python迷弟——可以说这部片子里包含的一百万个彩蛋我都可以很轻松的识别出来,并且报以会心一笑。
更不用说我现在在VR行业工作,日常的任务就是设计和策划VR体验,里面的那些VR行业的技术元素基本上就是我每一天工作需要接触到的东西。
如果你想要问诸如“《头号玩家》里的那些VR技术能不能实现”这种问题,大概全中国也找不到几个比我更加内行的家伙。
但是我还是不喜欢这部电影。
为什么?
我想那些赞扬这部电影的影评已经将电影的优点阐述差不多详尽了。
这部电影的最打动观众的地方,按照我所看过的很多评论,是这样的:「《头号玩家》对我们这些玩了这么多年游戏、看了这么多年电影,或者总的来说,享受了流行文化的这一代中国观众是一个承认——我们这么多年来的“玩物丧志”,并不是空虚徒劳的。
」它承认了我们的娱乐是一种有价值的行为。
对于从小到大背负着“玩物丧志”名号的中国中青年观众来说,这种承认简直是一阵清流,吹拂进了人的心里。
因为中国的青年太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这种承认了。
我想我不喜欢的核心,实际上就来自于这种承认本身。
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就会发现导演通过这140分钟的电影所塑造出来的这种承认本身,是站不住脚的。
让我们回到这部电影(也是原著)的剧情设定上来:天才的游戏设计师好乐迪(Halliday)创造了一个虚拟游戏世界“绿洲”,并且变成了世界首富。
他死后在游戏中留下了三个彩蛋,找到这三个彩蛋就能够继承他的所有财富,和“绿洲”的管理员权限。
于是全世界的所有人都投入到了对于他的研究之中。
而研究的对象,就是他所留下的一切痕迹:他的日常生活,他的过往历史,他所热爱的80年代流行文化,他玩过的游戏,看过的电影,听过的音乐……所有这些。
而邪恶的开发外设的公司IOI也通过组织的力量聘请了一大批这方面的专家来做这种研究,希望最后能够以此获得绿洲的控制权。
在原著小说里,作者毫无疑问是将自己代入到了这个首富天才设计师的身份之中了。
我几乎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脑袋里所转悠的狂热想法:有朝一日我成为了世界首富,我要如何如何——我要大家都听我的!
大家都喜欢我所喜欢的东西!
让大家都认同我!
你难道不觉得,这种想法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傲慢吗?
我们之所以热爱我们所热爱的东西,最大的原因恰恰在于它在本质上的“无价值”。
我们玩游戏是因为游戏有趣,我们也有很讨厌的游戏类型,那不去玩它就是了;我们看电影是因为电影好看,不好看的电影就不要去碰。
我们去做这些我们心甘情愿去做的事情,就在于这些事情是不产生价值的,它是消费的一部分。
而一旦消费变成了生产,那么游戏立刻就变质了。
万一我就是不喜欢《闪灵》呢?
万一我就是觉得Atari2600上的游戏古板无聊呢?
(说实话我并不相信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玩家会真心觉得那些古旧游戏有趣)你拿一个5000亿美元的胡萝卜在我头上悬着,逼着我去钻研这些东西,这不就是最最原教旨的资本主义吗?
天才设计师好乐迪在做这件事的时候难道不会想到,IOI的出现是一种必然,而且实际上是他的同路人呢?
将游戏从消遣变成生产,这就是最最原教旨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将人变成机器的过程,马克思将其称之为“异化”(Entfremdung)。
5000亿美元实际上就摧毁了这个游戏的一切意义,让它变成了机器生产的过程。
我们作为玩家会去嘲笑那些“只要充钱就能赢”的游戏,或者“你打到一个神奇戒指可以拿去换钱”的《贪玩蓝月》之类的页游,或者魔兽里的打金工作室(在《头号玩家》里的IOI就是这么一个组织),那把它改头换面成“游戏彩蛋”,怎么你就看不出来了?
从这个层面讲,好乐迪摧毁的不光是彩蛋游戏,他摧毁的另一件非常宝贵的东西,就是他自己赖以成功的创新精神。
我其实很难想象一个2045年的未来,在一个理应最有创造力的虚拟世界里,最流行的东西居然是上世纪80年代的!
拜托,这已经过了60多年了。
我们可以援引用宝树改编自道格拉斯·亚当斯的流行文化三大定律:a.大多数我出生时已经有的流行文化都是陈旧老土不值一提的b.大多数在我10-30岁之间诞生的流行文化都是无法复制的经典c.大多数在我30岁之后诞生的流行文化都是愚蠢肤浅,幼稚可笑的当然这是人类的共通心理(大概是进化论的结果)。
但是毫无疑问我们看到的是有个人把它当真了,而且还根据这三条定律写了一篇小说出来。
这篇小说就是《头号玩家》。
如上所述,这5000亿美元的巨型胡萝卜,不但是摧毁了游戏,也摧毁了创新精神。
所有人为了这个巨型胡萝卜在80年代流行文化的圈子里打转,那还有人会去创作出新的东西吗?
更重要的是,创新本身就是游戏精神的结果——探索未知,并且打开全新的领域。
创新和游戏本质上是一回事。
但是,为了琢磨好乐迪的内心,你看一千遍Monty Python或者只听有可能让你拿到5000亿美元的Duran Duran,这会让你做出任何新的东西吗?
太阳底下并无新事。
任何的创作者都是在前代作品的基础之上成长起来的。
冈田斗司夫在他的御宅文化论中,说过他们当年的科幻爱好者有一种“贵族的责任”(Noblesse Oblige),要去努力去吸收去钻研,去真正将作品融会贯通。
然后他们做出了《飞跃巅峰》,《蓝宝石之谜》和《王立宇宙军》。
对于前代作品的热爱的最顶级的方式,正是带着自己的趣味和偏好去创作出自己的作品,将这种趣味和偏好传递下去。
而好乐迪作为创作者本人,传达自己趣味和偏好的办法,却是5000亿美元——好乐迪亲手杀死了他自己。
从电影的层面,这也是同样的:电影里的彩蛋越多,实际上就越危险。
因为它仅仅是将过往的经典形象回收重新再利用,而不是创造出自己的全新视觉形象。
纵观好莱坞的历史,这些年来出现了一大批好莱坞的80年代“致敬”“怀旧”电影,比如《极盗车神》和《爱乐之城》,再比如《银河护卫队》《水形物语》。
这实际上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好莱坞(特别是科幻的那部分)已经很久没有推出原创的、辨识度高的视觉形象了。
《黑客帝国》有什么梗和彩蛋?
《银翼杀手》有什么梗和彩蛋?
《终结者》呢?
他们不需要致敬和梗。
他们就是被致敬的对象,梗的来源。
他们都能带来崭新的原创形象和突破的视觉风格,而近10年来的好莱坞,能做到这一点的科幻电影,可以说已经消失了(《银翼杀手2049》勉强可以算半个)。
而从电影里对于这些过往视觉形象的利用方法而言,也可以看得出,导演毕竟还是电影人,而不是游戏人。
毫无疑问,完成度最高、也是最经典的桥段是对《闪灵》的致敬。
导演抓住了《闪灵》的关键元素和桥段,这一段的致敬真的稳、准、狠。
个人觉得,可能除了斯皮尔伯格,没有其他导演可以完成(另一角度,就算有导演能够完成了,我觉得更可能会被喷到生活不能自理)。
但是游戏的彩蛋部分,就只能用浮皮潦草来形容了——可以说其中几乎全部的游戏梗,都只是一个皮肤的问题而已。
从这种角度,诛心而言,《头号玩家》的“1XX个彩蛋”,实际上可以算作是精心算计的,对于尽可能广阔的受众群做的一种收割。
电影中有很多迷影梗,这毫无疑问能够照顾到迷影群体;游戏梗,也照顾到了游戏群体。
而电影剧情最后让大家回到现实之中,又确立了一个很轻巧的,很符合主流价值观的结尾。
于是,所有人都皆大欢喜了。
《头号玩家》就是这样一个“所有人都皆大欢喜”的作品。
它不是科幻,而是一个童话——这也是斯皮尔伯格所擅长的类型。
《ET》和《AI》都是这样的在科幻设定下的童话故事。
它是一个轻盈的仿佛梦幻的故事,正好与它所致敬的80年代电影相同。
所以,这是一场梦。
梦醒了,大家也就结束了吧。
10 ) 彩蛋背后是斯皮尔伯格更重要的游戏哲学:你是要赢?还是要玩?
现在头号玩家好像被评论捧成了一个“彩蛋电影”或者“情怀电影”,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斯皮尔伯格只是把这个电影拍得很轻松,但这份轻松,可完全不和“简单”划等号的。
关于斯皮尔伯格,最重要的一个评价是:“斯皮尔伯格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导演,因为他喜欢的东西,全世界都喜欢。
”所以他拍电影常常呈现出一种天真的“顽童感”,看起来就是释放了自己最本真的一面,可是他内心的这个纯真顽童,恰好是全世界观众口味的公约数,讨人喜欢又不用拧巴自己。
但这次真正令人感到惊愕的是,拍游戏主题(却又不是游戏改编IP)这么难的主题,他还是做成了。
在主流视野里,讨好亚文化,小圈子,可以说是最最困难的一件事。
小圈子里的鄙视链,可以陡峭过珠穆朗玛峰。
圈子内经常撕来撕去的是:我比你核心,我比你正宗,我比你进圈早。
然后圈子里的人再一致对外:你不是我们圈的,你拍这个东西不伦不类,不要扭曲和代表我们。
如果我们把游戏玩家分成:核心玩家(各种大作都玩,游戏主机一堆);轻度玩家(喜欢的游戏会玩一玩,但瘾不重);非玩家(几乎从来不玩游戏)三个细分群体的话,头号玩家这次做到了成功征服核心玩家和轻度玩家,并让非玩家觉得这电影没这么神,但片子还是不错的。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讨好非玩家群体反而是容易的,因为他们不怎么玩游戏,也对游戏不太感兴趣,所以他们的游戏观很容易塑型。
对他们而言,进电影院是看了一部合格的好莱坞大片。
最差的意见也不过是“我对这个主题不感冒,现在评分这么高是不是过誉啊?
”而搞定现在给电影最多好评的轻度玩家和核心玩家就不那么容易了,尤其轻度玩家数量巨大,是本片最大的目标群体。
如果电影讲的宽而浅,核心玩家会觉得无聊;如果电影讲的窄而深,又会变成小圈子的狂欢。
斯皮尔伯格是怎么搞定的呢?
重头戏在游戏的三个关卡上。
这三个关卡代表了非常重要的三种游戏类型:赛车竞技,冒险解谜,动作角色扮演(也可以看成无双或者大乱斗)。
斯皮尔伯格用了他擅长的体验式的电影拍法,呈现了一场豪华版的“我在电影院看游戏直播”。
他跳过了“玩家的操作水平”这一门槛,直接把游戏最精华的乐趣打包呈献给观众。
第一关,赛车游戏。
赛车游戏的精华是分秒必争的紧迫感,路边绚丽景色呼啸而过的畅快,以及躲避路障和吃金币和道具之间的权衡。
在这个炫目的开场里,他把这三个要素都顾及到了,所以不管是经常玩游戏的人还是偶尔玩游戏的人,对这个观影体验都无话可说,只有赞叹“这个游戏味做得正!
”
第二关,冒险解谜游戏。
第二关借由闪灵这个恐怖故事的壳子,但实际上是把恐怖电影改装成了寂静岭,古墓丽影一类的带有恐怖氛围的冒险解谜游戏。
这类游戏的核心是惊悚的恐怖氛围,带有些许温情的结局真相,想破头皮也想不出来,却在阴差阳错间破解关键的障碍谜题。
斯皮尔伯格再一次,check√,check√,check√。
就问你,拍得这么像游戏的电影,服不服?
第三关,多人在线角色扮演(大乱斗)。
第三关的游戏是一个大杂烩。
队友间的配合像魔兽世界,两军对垒疯狂斩杀像三国无双,不同时空下的IP角色同时出现像大乱斗。
这一段的高潮点当然是高达的出现,高达的出现很像两军对垒的焦灼状态下我方后方队友憋了一个逆转战局的大招。
为什么高达的出现让很多人泪目?
一方面固然是熟悉的IP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引人入胜的战局早已把观众的神经崩得紧紧的。
高达的出现融合了队友的友情,对游戏奇观的赞叹和逆袭的畅快淋漓。
这不正是游戏的魅力吗?
所以斯皮尔伯格拍游戏令人叹服,绝对不是仅仅凭借100多个彩蛋而已。
他是一个真正了解游戏魅力的人,并且借助电影手段,把游戏的精华和感官刺激,加倍放大呈现在了大银幕上。
但是,除了游戏在感官上的刺激,他对于游戏也是有自己的哲学思考的。
虽然他为了拍出更好玩更轻松的商业片,没有想把这些挖得很深,但是他对于“游戏”这个产品的定位和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游戏”这一人工精神消费品的态度,都埋在了三个关卡解谜线索里。
仅仅把游戏拍得炫目就够了吗?
显然不是。
家长,孩子,玩家,非玩家,几波人到电影院去,电影对于游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经得起各个角度的检验。
斯皮尔伯格的游戏哲学到底是怎样的?
首先,电影最大的主线,通关赢奖这件事,本质上只是一次夺宝奇兵吗?
创造了绿洲的游戏之神哈利迪设计的这些关卡只是在考验挑战者对他的生活八卦的了解程度吗?
当然不是,这三重关卡是在帮他筛选继承人。
而这个继承人继承的不仅仅是他的财富,还有绿洲的未来,所以反派诺兰即使投入了再多人力物力,他也还是赢不了。
哈利迪安排的游戏关卡注定要把他不认同的游戏观念筛掉。
第一关的线索是:游戏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规则,应该是不同的,甚至可以相反的。
游戏世界不应该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和还原。
这一点往小了说,是游戏设计的想象力。
游戏的很大一部分乐趣来源于它对我们想象力的刺激,以及我们对于游戏制作者伟大想象力的惊叹和追随。
如果连游戏这么本应天马星空的世界都像现实世界一样中规中矩,还要游戏做什么?
现在的游戏机机能越来越强,越做越拟真,但我们玩家想要的是一个好玩的游戏,而不是翻版的现实。
往大一点说,游戏世界的想象力和反常的规则,定义了现实与虚拟的界限,把现实的真,和游戏的假,做了切割。
电影中间一幕,主角一行人黑了反派诺兰的设备,模拟了他的现实环境,让他身处游戏中,却以为身在现实。
这说明以电影发生的时代的技术,模仿以假乱真的现实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但是绿洲的画面依然是我们看到的炫目的超现实感。
这是哈利迪的选择。
任何玩家,一眼就能看出来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游戏。
第二关的线索是:虽然虚拟的游戏世界很爽,我们要正视现实世界,因为那才是真实。
哈利迪在虚拟的游戏世界里呼风唤雨,但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却有巨大的遗憾。
他此生挚爱是他唯一约会过的女生,他因为自己的怯弱没有迈出关键一步。
他把这个遗憾埋在了游戏里。
只有懂得这个遗憾的人,才能度过这一关,而玩家过了这一关,就一定会受到灵魂触动,重新反思自己看到的游戏世界。
这一点与尾声处,童年的哈利迪走出游戏的房间是呼应的。
那不是一个普通的防沉迷系统,哈利迪希望未来“绿洲”的管理者明白,游戏世界是假的,虽然它给玩家带来了高度提纯的快乐,但那只是一颗糖,糖不能当饭吃。
游戏世界不能替代现实世界,我们依然要投身真实的喜怒哀乐。
因为在生命的最后,游戏世界里的所有成就,都不能弥补现实生活中的遗憾。
哪怕生活它并不完美,但它真实。
真实,要比游戏里的快乐,更有重量。
游戏世界再炫目,它只是现实世界的补充而非替代。
这一点和骇客帝国的价值观非常相似,但是它被讲述的方式是糖果味的,它不像骇客帝国那样黑暗和沉重,而是被包装成青少年式的,易于消化的版本。
第三关的线索是:游戏的核心价值,是“赢”还是“玩”。
第三关讲的是最重要的一点,电影的正反两派到底在争什么?
如果只是简单在争哈利迪的财富,那么两方的立场应该都是中性。
可为什么在电影里面,主角们一方是有正义光环的?
反派们看起来如此邪恶?
因为他们有一个核心分歧——游戏的价值取向,应该是“赢”还是“玩”。
如果游戏的价值取向是“赢”,游戏世界会变成现实世界的残酷加强版。
游戏中的玩家碾压,会加倍释放出参与者的恶念。
反派诺兰的IOI都做了些什么呢?
“氪金玩家”主宰世界,非氪金玩家沦为IOI里穿着一样,行为一样,彻底丧失个性的牲畜玩家,在现实生活中财富平平的玩家为了氪金深陷债务,为了赢取胜利,不惜出卖队友等等……也就是说,如果技术被不好的价值观所统领,它非但不能为我们生活带来好的改变,相反的,技术进步反而会加速释放人性的恶,让剥削和压迫更加沉重。
为什么女主角带领的一群人叫“反抗军”?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一旦游戏世界被IOI的价值观统领,更多的玩家参与者将落入深渊。
而哈利迪和斯皮尔伯格心目中的完美游戏世界不应该是这样,所以他们选择了把游戏的核心定义为“玩”的一群人成为最后接班人。
因为以“玩”为目的游戏,激发了他们心中的善,让他们往人性更好的一面前进。
孤独的孩子有了朋友,孤僻的宅男有了恋人,生活中不如意的loser有了快乐。
最后的大乱斗里,每个玩家都拥有自己丰富的游戏形象,千人千面,而没有朝着单一的“强”的方向去进化。
每个人都能从游戏的世界里分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因为价值是“玩”,就有了多样性,有了多样性,就有了个性化的幸福体验,这样的世界,才能惠及最多的人。
千人千面的游戏世界现实生活已经让人筋疲力尽了,如果游戏的世界里还不能喘口气,还要去争一个“赢”字,那还要游戏的世界做什么?
所以IOI,诺兰是一定不会在绿洲里胜利的。
哈利迪也好,斯皮尔伯格也好,他们心中的游戏哲学就结尾:“谢谢你玩我的游戏。
”而不是“谢谢你赢了我的游戏。
”在电影的结尾,男主角的那一滴泪,也应该奉献给每一个游戏人:谢谢你们带给我快乐,而不是压迫我,榨取我,利用我,鄙夷我。
在一个快乐的游戏里,我们的关系理应像这两位赤子,惺惺相惜,山高水长。
————本文原载于我的公众号肖恩恩恩恩肖的瓜子社(Sean_lalala),欢迎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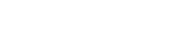


































































前面一直很好,诺亚捡起耳钉的那一刻,光照在他们的脸上,真的很棒。但是后来的冲突来得太突兀,结束的也太仓促。如果按照前面的节奏,再配上女主的音乐,真的很好。
不喜欢女主,感觉很渣对朋友自私,但适合周末放松心情哇。
看前面会奇怪女主为什么会和那个蠢渣男在一起十年,看后面会觉得they deserve each other。以及2014年了还要靠看到意中人和别的男/女人在一起来制造误会推动剧情,通过电台表白心迹………
男女猪脚颜值高配,剧情一般……
对那首纯音乐念念不忘,有知道的告诉我一声
Follow the river, down to the sea.
女主三观不正,period
纽约女郎乡下情
童话般的爱情故事...看到中间的时候 给的四颗星,结尾给了2颗。傻白甜也能有爱情,无语,傻逼的爱情故事
乡村音乐很好听,推荐片尾曲~PS.爱奇艺上翻译成 纽约女郎乡下情…怪不得找不到
布兰特妮·斯诺在这部电影里出现过吗。。?
这比我期待的要好很多倍我最后按我爸爸说的那样生活永远不要背叛爱情至上如果失败了 就回到伍德斯托克
“我没有在逃避,我在找回一些东西。”“光射到它上面,照亮了我。有些事很难被无视。”“有时候感到奇怪总比悲伤要好。”“你知道吗他之所以爱你,是因为他得到了你。”我算是明白了要成为独立音乐人,一定要吉他本当上手。美国人道歉总是很容易。为什么我不行。十年前的片子但节奏轻快。女主很美像很多有名的女演员却没有火,火真是看命啊。菀菀类卿也没有火过。
跟伍德斯托克有什么关系?除了结尾的那一句话
把时间浪费在这样狗血的电影上,真是可惜了我的时间。也毁了对于伍德斯托克这个美好地方的印象。F...!
Jameswolk太gentle了,一看果然八年前的片应该也还是翻拍,现在很少有这种传统温柔风格男主了。ost也很棒,女主真的很巨婴。
想评三星半的,发现没有,男主蛮帅的,题材比较老套,没什么新意,大团圆结局
反着来一部“乡下女孩北京情”
有谁知道片尾曲吗
歌曲比电影好